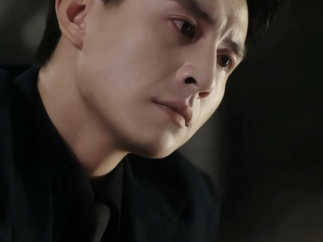流水线上的手指刚刚结束十二小时的机械劳动,此刻又在手机屏幕上疯狂滑动。霸道总裁粗暴地抬起她的下巴,背景音乐骤停,画面定格在她屈辱而迷离的眼神——黑屏跳出“VIP解锁后续”的刺眼按钮。这一刻,受众几乎不假思索地点击支付,吞下又一口资本精心调制的精神鸦片。
劳动大众正生活在一个被流行短剧重新定义情感节奏与阶级认知的时代。当“5秒抓人、10秒反转、30秒高潮”成为资本收割注意力的行业金律,当算法比我们自己更懂得如何撩拨被压抑的神经,这场针对以打工者为主体的全体劳动者的注意力狩猎,已经悄然改变了我们感知自身处境的方式。那些看似自由的指尖滑动,实则是劳动大众在异化劳动后的二度异化——在消费中继续被资本剥削。
一、资本的意志:短剧如何成为财富积累与注意力控制的异军突起?
短剧的异军突起,绝非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资本在快节奏时代找到的最富渗透力的财富积累工具。它不仅是娱乐工业的延伸,更是资本创造出的一种新型控制机制——通过算法精准控制注意力,将劳动大众的碎片时间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利润。
按市场决定的自发规律,各类资本都遵循着同样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资本决定着什么样的内容能够被生产、传播。而养家糊口的以打工者为主体的劳动大众,在剧中往往被刻画为两种极端:要么是逆来顺受的草芥,等待霸道总裁的救赎;要么是心机深沉的爬升者,在等级秩序中不择手段。打工妹永远依靠总裁的垂青才能改变命运,这种叙事巧妙掩盖了现实中的阶级矛盾。如同清末的鸦片,只不过形式从植物鸦片变成了短剧,从鸦片枪和鸦片馆变成了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平台,都是通过让人上瘾来实现某种控制,当代短剧以娱乐休闲为外衣,其隐蔽性和渗透力更强。
短剧的崛起体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的极致表现——“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流行短剧正是这种资本对社会联系普遍占有的表现,它不仅占有劳动大众的闲暇时间,更占有他们的注意力、情感和欲望。通过精准的算法推送,资本控制着劳动大众看什么、想什么、感受什么,从而实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普遍占有。
短剧流行内容首先对阶级意识系统性消解。《重生之我在流水线》这类看似为劳动大众发声的作品,最终往往落入“逆袭成为人上人”的陈旧套路,它所肯定的仍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非劳动者的尊严与团结。在《豪门恩怨》中,劳动大众的存在不过是衬托豪门权势的背景板,他们的挣扎与抗争被简化为“攀附上位”的投机,而真正的阶级压迫与团结斗争却被彻底抹去。
多数短剧对劳动价值的彻底否定更令人心惊。在《财富游戏》这类剧中,财富的积累与劳动无关,只与心计、运气、婚姻相关。劳动大众在剧中的价值永远通过攀附实现,自身的劳动技能、专业素养变得无足轻重。这种叙事和经济学界有人放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祸国殃民”的怪论紧密响应,瓦解劳动认同感——既然“努力不如嫁人”“技能不如心计”,那么流水线上的辛苦付出又有何意义?
对消费主义狂热鼓吹则是流行短剧常见的另一重陷阱。《买不起的爱》表面上批判拜金,实则强化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名包、豪车、豪宅成为人生赢家的标配,通过剧中人物的消费得到了替代性满足。当短剧里的“霸总”随手送女主一套别墅,而现实中的劳动大众连房租都要分期支付时,不愿婚育,这种强烈的对比不仅制造了虚幻的优越感,更让劳动大众对自身处境的愤怒被转移为对“暴富”的幻想。
更值得警惕的是情感的被殖民化。流行短剧培养了一种情感速食主义——在《困在系统里的数字民工》中,外卖员疲于奔命,唯一的慰藉就是在休息时刷着逆袭成功的短剧——这种讽刺性的画面正是当代劳动大众处境的隐喻,在现实中为资本算法创造剩余价值,在休闲中又为资本贡献流量和付费,甚至欲望和幻想都被资本支配。
这是美国主导的虚伪“普世价值”全球思想殖民的微型镜像。美国文化工业用“英雄救世”“逆袭翻身”“爱情至上”等套路,让受众在无意识中接受“个人主义至上”“阶层流动必然”“物质幸福终极”的虚假价值观,进而消解对结构性压迫(如阶级固化、资本垄断、社会不公)的批判意识;而流行短剧则通过“霸总救赎”“打脸复仇”“30秒反转”的工业化配方,制造出更碎片化、更易上瘾的情感代偿——失去了对现实苦难的深刻共情(如对工友失业的漠视、对加班文化的麻木)。前者通过宏大叙事实施思想渗透,后者通过微观情节完成情感操控,二者逻辑完全一致:通过控制人的精神世界,让被压迫者主动认同压迫的合理性。每一次“心动解锁”“付费追更”,都是劳动大众自愿为这种思想殖民支付的“情感税”。
二、历史的警示与文化的觉醒
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列宁晚年的思考显得尤为迫切。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社》中写道:“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晚年的列宁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最艰巨的任务是文化领域的斗争,是要在精神上彻底摆脱旧世界的枷锁。而毛泽东晚年的实践,特别是他对至今充满激烈争议的文化革命的高度重视,也源于类似的判断——如果不能打破剥削阶级的文化霸权,社会主义就可能在糖衣炮弹中变质。
短剧作为当代最富渗透力的大众文化形式,恰恰是这种文化斗争的主战场。流行短剧观众越来越意识到,当在短剧中看到的永远是“阶级跨越靠嫁人”“劳动无用靠心计”的叙事时,最终只能在虚拟的“爽感”中麻醉自己,成为资本最温顺的消费者。
三、劳动大众的文化突围:从“被喂养”到“自主创造”
那么,劳动大众的文化出路何在?重温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毛泽东),就知道习近平提出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是针对当前形势切中时弊的判断。
劳动大众需要找回文化阵地的主导权。这并不意味着拒绝所有短剧——正如无产阶级从不拒绝学习资产阶级掌握的技术,而是要学会辨别、改造与创造。例如提炼“三十秒翻转”、适应时间碎片等在信息时代吸引大众的手法,制作红色短剧、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将短剧这一形式转化为传播阶级意识、弘扬劳动价值的工具。我们可以鼓励工人自媒体创作真实职场故事,用短剧的形式展现流水线上的团结抗争、外卖骑手的互助温暖;可以推动社区影院放映反映劳动者生活的纪录片,让劳动大众的真实经历被看见、被听见;甚至可以在企业内部开展“工人创作大赛”,让一线员工用镜头记录自己的生活,用故事传递对公平与尊严的诉求,用具体的艺术形象表达“码农”等底层脑力劳动者对劳动创新成就的喜悦。
更重要的是,劳动大众需要在现实中重建团结与抗争的意识。当我们在短剧中看到“霸总救赎”的幻想时,不妨转身走进车间读书会,与工友讨论《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价值的论述;当算法推送“逆袭爽剧”时,不妨在出租屋里与邻居聊聊如何通过工会争取合理的加班费;当消费主义鼓吹“奢侈品=幸福”时,不妨组织社区活动,用集体力量争取更公平的住房与医疗资源。文化的觉醒,从来不是停留在屏幕前的“批判自觉”,而是转化为现实中的团结行动——因为真正的文化武器,从来都是服务于阶级解放和劳动为主体的实践。
四、结语:按下暂停键,夺回注意力主权
曾几何时,美国植人网文嘲讽我们注意了纸媒,忽略了网络,为在网络潜伏进大批带路党两面人而得意,而美国国务院也公开宣示要依靠中国的内部力量。如今又到了短剧替代连续剧大部头制作,手机逐渐取代电视的转折点,重视短剧生产消费,反映劳动大众的文化斗争,从来不是简单地拒绝娱乐,而是要在娱乐中注入阶级立场,用新技术传递劳动大众的声音;不是被动接受资本定义的“爽感”,而是主动创造属于劳动者自己的“真实”。当我们学会在短剧的喧嚣中按下暂停键,当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劳动的故事,劳动大众的文化觉醒,对西方思想殖民的拒止,便从这一刻真正开始。
【作者注:剧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不针对任何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